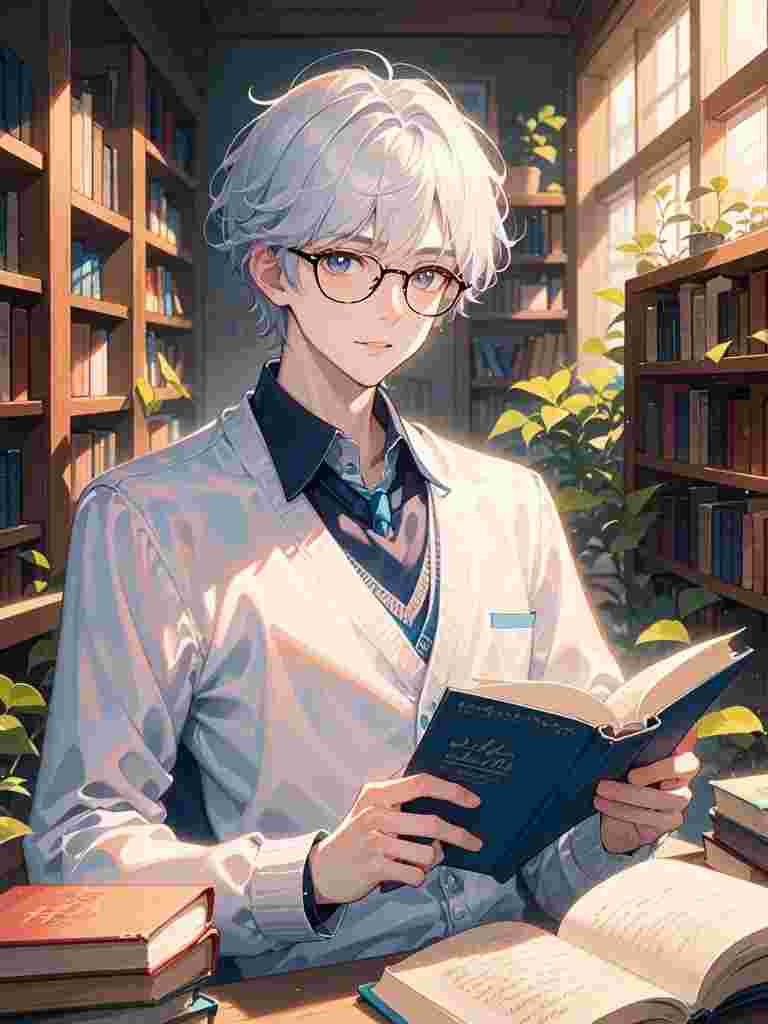第7章
我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走出时,阳光刺眼得让我睁不开眼。
凌辰疯了一样冲出来,白大褂上的褶皱里还沾着林薇薇哭闹时蹭上的泪痕。
他想抓住我的手腕,我侧身躲开,骨灰盒在怀里硌得肋骨生疼。
“晚晚,你听我解释……他的声音劈得像被扯断的琴弦。
“我已经让律师收集证据了,林薇薇至少要判十年。
你要什么补偿,我都给你……补偿?。
我低头看着怀里的骨灰盒,母亲的照片在阳光下泛着冷光。
“凌辰,你知道我妈走之前最后说什么吗?
她问护士,‘我家晚晚的腿还疼不疼’。
他的脸瞬间褪成纸色,踉跄着后退半步,后腰撞在石栏上。
我记得三年前他也是这样,在医院走廊里被林薇薇哭诉着拉住,看都没看我打了钢板的腿。
“我每周去给她扫墓。
他突然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般的语气,“我把所有财产都转到你名下,我……不必了。
我转身走向公交站,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格外清晰。
“你最好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,脏了我妈的清静。
公交车到站时,我听见身后传来金属落地的声响。
凌辰僵在原地,白大褂被风掀起边角,像只折了翅膀的鸟。
搬家那天,张主任特意派了两个护工来帮忙。
我只带走了母亲的遗物和一箱旧书,凌辰送的那套公寓钥匙被我留在茶几上。
上面还挂着他当年刻的情侣挂坠——如今看来像个笑话。
护工说,凌辰这几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,调出了所有监控录像反复看。
林薇薇的律师来取保候审时,他直接把一沓伪造处方的证据甩在对方脸上,冷笑说“让她牢底坐穿。
“苏小姐,凌医生他……护工欲言又止,“昨天在ICU门口站了一夜,手里攥着你妈最后一页病历,指甲都嵌进纸里了。
我把母亲的毛衣叠进箱子,袖口磨出的毛边刺得指尖发麻。
这件枣红色的羊毛衫,是去年冬天我陪着母亲织的。
她总说凌辰穿白大褂太素净,想给女婿织件贴身的。
公交站台的广告牌换了新的,上面是凌辰作为杰出医生的宣传照。
他穿着笔挺的西装,胸前别着医学会的徽章,笑容温和得像从未经历过这些龌龊。
我盯着那张脸看了三站地,直到广告被另一辆公交车挡住。
才发现自己的指甲已经掐进掌心。
三个月后,我在南方小城租了间带阳台的房子。
楼下有个菜市场,每天清晨都能听见商贩的叫卖声。
母亲总说喜欢这样的烟火气,可惜她没能等到。
凌辰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。
张主任打电话说,林薇薇的庭审上,凌辰亲自出庭作证,播放了她偷换药物的监控录像。
她被判刑十二年,入狱那天在法庭上疯了似的咒骂,说要拉着凌辰一起下地狱。
“他把医院股份全卖了。
张主任的声音透着疲惫,“天天守在你原来住的小区门口,下雨天都站在树下……张伯伯,我打断他,手里正给母亲种的绿萝浇水。
“我下个月要去考教师资格证了,以后别跟我说他的事了。
挂了电话,绿萝的叶子上还挂着水珠。
我想起小时候母亲教我浇花,说“浇水要浇透,做人要做真。
可惜我花了三年才明白这个道理。
深秋的一个傍晚,我去超市买白菜时,在收银台撞见了凌辰。